证明标准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多层次的综合系统。因此,有必要根据不同主体、不同层次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一是根据证明主体的不同区别适用证明标准。上海刑事律师来讲讲有关的一些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不仅仅只是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这就需要对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设定一个标准。对此,可借鉴英美法系关于不同证明主体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成熟做法,即对控方的有罪证明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被告方则采用“优势证明”的标准。
也就是说在被告人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被告人不必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只需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即可。很显然,“优势证明”是比“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更低的证明标准,如此区别适用,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一致的。
一般而言,对犯罪事实的全部构成要素都需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排除合理怀疑”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故还应将其作为证据充分性与确实性的衡量标准。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考虑,没有对个别证据或者局部事实的“排除合理怀疑”,则对全案证据与案件整体事实的“排除合理怀疑”也就丧失了其前提基础。
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非仅仅适用于最终地对全案事实的综合判断,在对个别证据的确实性或局部事实的认定进行判断时,同样可以参照“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范围还包括对合法性的判断,且“排除合理怀疑”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更为适用,排除程序本身性质更适合“排疑”的消极方法。因为证明证据非法很难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只要能够对证据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相关证据就应当排除。
毕竟在刑事诉讼中,是由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被告方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如果对被告方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就相当于变相减轻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二是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区别适用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对象既包括实体法方面的一些事实,也包括程序法方面的一些事实,既包括定罪事实也包括量刑事实,既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也包括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这些事实在整个案件中的地位、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而证明标准也不应完全相同。
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准确地说是对案件实体法事实中定罪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至于量刑事实和诉讼程序中的某些事实,比如,回避、强制措施、违反法定程序等则在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立法进行适当完善。其一,需要明确量刑事实所适用的证明标准。
一般而言,由于量刑事实属于实体方面的事实,因此,一般应适用十分严格的证明标准,即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如果属于减轻被告人刑罚的情节事实则进行自由说明即可,无需严格证明,即不需要通过严格的证据和严密的调查程序就可以得出的证明,这也符合当前有利于被告的立法精神。
其二,作为程序法方面的某些事实,如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程序等,也只需达到自由证明的程度即可,无需严格证明。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准确适用,因为它混淆了“排除合理怀疑”与“唯一结论”和“排除一切怀疑”的概念。因此,深入研究"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完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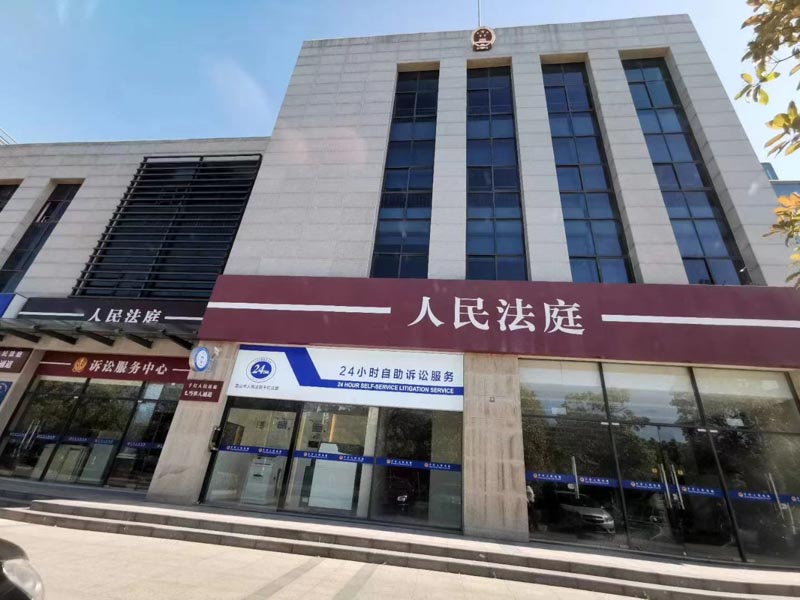
总之,上海刑事律师发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对于进一步明确证明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功能。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