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刑讯逼供之外,究竟哪些非法取证方法可以或者说应当纳入“等”字所指范畴,具体判断和认定的标准又该怎样理解和把握皆是问题。在本案中,被告人章国锡曾辩称:侦查机关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严重违法,采用了疲劳审讯以及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获取其有罪供述。上海专业刑事律师为您讲解一下有关的情况。

那么,“疲劳审讯”是否应纳入“等”字所指范畴予以禁止?而侦查机关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性手段获取证据又是否应一律认定为以非法方法取证?
第四,程序问题。也就是说,程序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如果被告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在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下,辩方是否也应分担部分举证责任?控方如何证明所获证据的合法性?如何把握案件的证明标准?
第二,概念问题:是缺陷证据,还是非法证据在本案一审程序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曾辩称:2010年7月22日10时左右,被告人章国锡被反贪局侦查人员控制,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因而是非法的。但显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主张与法院在判决书中的认定存在一定差距。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的前期侦查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因而构成违法侦查,所收集的证据也构成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而法院在判决书中仅认定侦查机关的前期侦查行为存在瑕疵,所形成的证据为瑕疵证据而非非法证据。
从证据法理上讲,“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首先,在性质上,“非法证据”系侦查机关以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而“瑕疵证据”虽同属侦查机关以违法方法获取之证据,但违法程度较轻,并未严重侵犯公民人权。
形象地说,“非法证据”属于不可原谅之“大错”,而“瑕疵证据”则属于可原宥之“小过”。其次,在效力上,“非法证据”自始即无证据能力,一经查实即应从程序上予以排除。而“瑕疵证据”则属于效力未定的证据,是否有效取决于该证据的瑕疵能否被补正或合理解释。
若瑕疵证据的瑕疵经补正或合理解释而消除,则瑕疵证据可转化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具有可采性;若瑕疵证据的瑕疵无法补正,则该证据将转化为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具可采性。我们注意到,在本案审判过程之中,法官并未径直将侦查机关的前期侦查行为定性为违法侦查行为,而是一再要求控方对证据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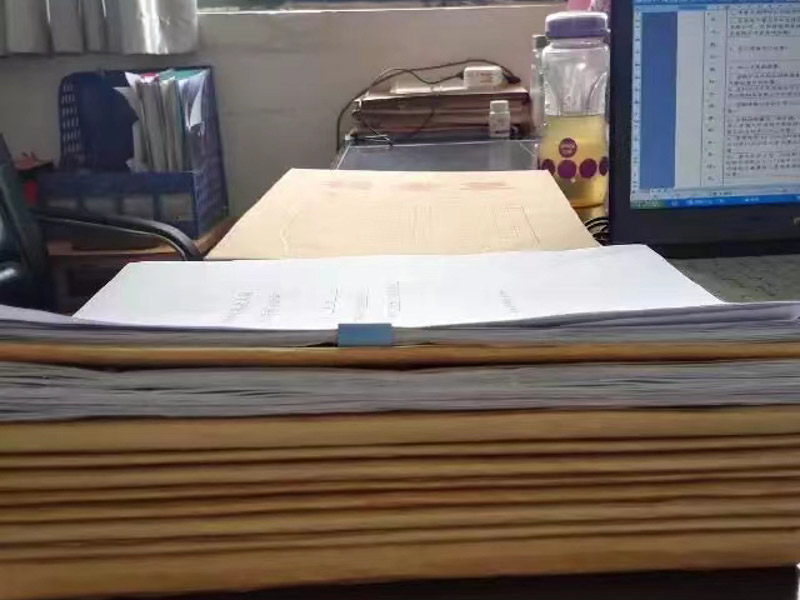
这表明,法官更倾向于认定侦查机关的前期侦查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但尚不足以构成非法取证,只要控方能够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法官仍愿意采信该证据。只是因为控方始终无法向法庭补充提交东钱湖纪委找章国锡谈话的笔录或其他证据以证明纪委《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消除证据的瑕疵,法院才最终否定了上述证据的效力。
问题是,法院的上述判决和裁定是否正确?从证据法理论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通过前期调查形成的证据究竟是非法证据还是有缺陷的证据?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答案必须逐一界定,找出以下问题。
首先,本案的前期进行侦查工作行为影响究竟是纪检监察管理机关的违纪学生调查研究行为,还是中国检察监督机关可以实施的初查行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对于纪检监察行政机关通过调查以及办案并无需遵守国家刑事诉讼法关于公司立案、侦查等相关法律程序之规定与要求,因而,若本案前期侦查活动行为是否属于我们纪检监察审计机关根据调查办案,检察机关仅仅是一个协助,那么就无所谓违法的问题。
但是,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虽然控方向法庭提交了东钱湖纪委的《情况分析说明》,试图证明本案前期侦查犯罪行为系纪检监察机关对章国锡违纪情况的调查社会行为。

上海专业刑事律师发现,由于控方无法向法庭补充提交东钱湖纪委找章国锡谈话的笔录或其他证据以证明纪委《情况具体说明》的真实性,法院系统最终得到否定了该证据的效力。因此,本案的前期市场调查结果行为能力应从实质上解释为检察机关的初查行为。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