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持“地下偷窃说”者将抢夺罪限定解释为对物应用暴力牟取被害人缜密占领的财物,然则按这一规范来区别盗窃罪与抢夺罪依然存在不明确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牟取财物的行动在客观上并无造成职员伤亡的实践效果时,要想判别此种牟取财物行动有无造成职员伤亡之可能性,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太大概操纵的”。闵行刑事律师带您了解一下有关的内容。

即便觉得掠夺行动拥有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可能性,也不去不及消除偷窃行动有大概针对被害人缜密占领的财物(如针对被害人处于晕厥状况而使劲夺取其手中紧握的财物)而拥有侵占人身权利的可能性。就连持“地下偷窃说”者也承认,盗窃罪并不以采取平和非暴力手段为前提,行为人以暴力方法取得财物,但又没有达到使他人不能抗拒的程度,只能认定为盗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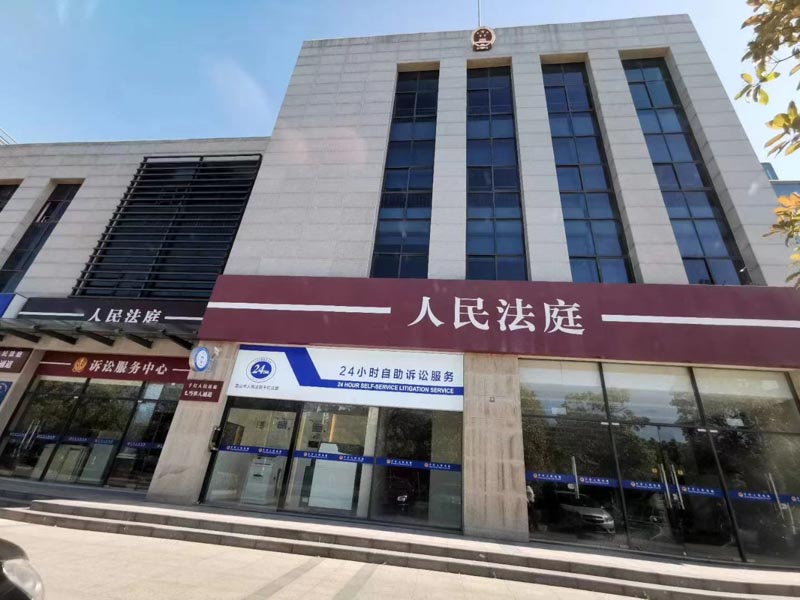
如果说抢夺是对物使用暴力具有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的危险性,那么当着被害人的面公然取走财物更具有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的可能性,因而应被认定为抢夺罪。持“公开盗窃说”者将抢夺罪限制解释为对物使用暴力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是其担心被指责混淆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而特意做出的限制。
持“地下偷窃说”者罗列的上述案例的定性并未在我国的审讯实践中失掉认可。在上述案例1中,持“地下偷窃说”者并无供应审讯构造将近似的行动认定为盗窃罪的实在司法规。实在,近似的行动在审讯实践中普遍都被认定为抢夺罪。比方,被告人舒某离开珠宝商铺装作购置项链,当雇主林某拿出一条黄金项链给其试戴时,舒某将项链戴在脖子上即时逃脱。舒某被捕归案后,人民法院认定其行动组成抢夺罪。
从案例2看,行为人的行动被认定成立盗窃罪并不能解释审讯构造抵赖偷窃能够接纳地下的体式格局举行。在该案中,应当觉得甲、乙、丙三人在单元向导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合偷窃了工场的财物,其行动依然属于隐秘盗取。
在法律实践中,近似的行动普遍也都被认定为盗窃罪。比方,被告人陈想平与肖高超常在一路吸毒,后两人因无钱购置福寿膏,陈想平向肖高超倡议去本人家里偷取黄花菜调换毒资。肖高超暗示批准以后,陈想平先从自家将黄花菜偷出,然后由肖高超担任接应和贩卖。人民法院认定二人的行动仍属于秘密窃取,成立盗窃罪。其理由是二人是在陈想平的其他家庭成员不知晓的情况下盗走了黄花菜。
对于案例,审判实践中尚未出现类似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罪的判例;相反,类似的行为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都被认定为抢夺罪。例如,被告人曲某翻窗进入张某房间,因在开启房门反锁装置时弄出响声惊醒了张某,张某大喊,曲某未予理睬并拿走张某的大量财物。人民法院认定曲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
笔者并不反对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但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盗窃罪的理由仍在于其行为的秘密性,而并非承认盗窃可以采用公开的方式进行。在本案中,行为人采用欺骗的手段将被害人骗下车,然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财物据为己有。即使事后被害人知道行为人拿走了他的财物,也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盗窃罪,行为人控制、转移财物仍然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
以实益为规范区别盗窃罪与抢夺罪在必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罪刑倒挂”的题目,但也会带来新的题目。比方,前述论者觉得“入户偷窃、照顾凶器偷窃、扒窃”入罪无数额的请求,并进一步指出既然“隐秘型”的“入户偷窃、照顾凶器偷窃、扒窃”未达“数额较大”都组成犯法,那么“地下型”的上述行动更应该组成犯法,进而主意“地下偷窃说”。

闵行刑事律师认为,这里的问题是,觉得“入户偷窃、照顾凶器偷窃、扒窃”入罪无数额请求的观念曾经遭到我国刑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批评,而以这类遭到批评的观念为前提来重新划分偷窃与抢夺罪的合用局限就更不值一驳。有学者的实证研讨结果注解,我国刑法给盗窃罪设置了显然太重的法定刑,就行动的社会危害性与配刑之间的瓜葛而言,盗窃罪的法定刑较之抢夺罪的法定刑更加严格。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