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立法中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发展十分重要的价值管理功能,彰显了我国对于司法的时代性与进步性,但由于诸多方面原因,这一技术标准在司法工作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存在适用不好把握等方面分析问题。上海刑事辩护律师为您解答一下有关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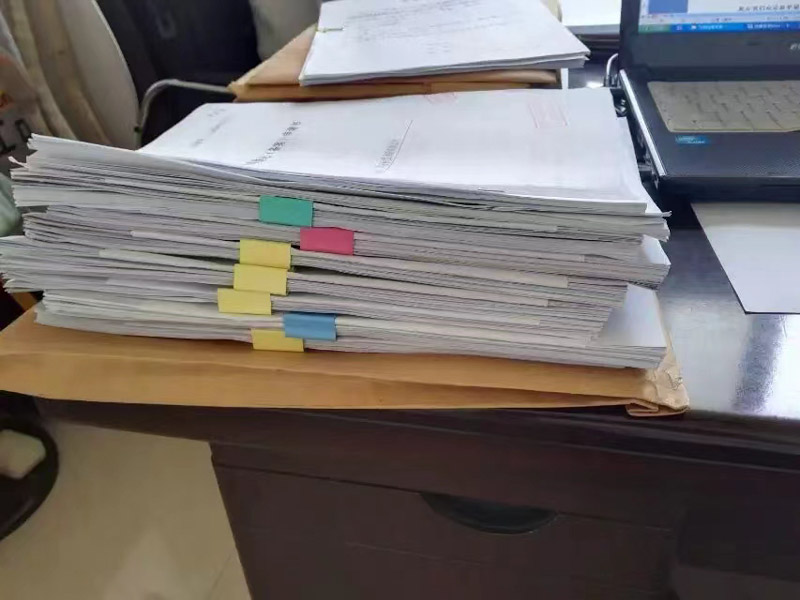
一、“无合理怀疑”概念与“唯一结论”“无一切怀疑”概念相混淆
“结论唯一”的内涵问题认识不一,从“结论唯一”表述出现的几次情况看,都是和“排除合理怀疑”同步出现的。
如在2006年11月份隆重举行的第五次全国性的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之上,最高法院长肖扬同志解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含义,指出:“特别是影响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存在一定的疑问,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进而得出唯一结论的,均应严格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无法成立的无罪判决。”
在这里,“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结合在一起,被提了出来。随后,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又将“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一并提出,在第5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均有证据去证明;
(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进行查证属实;

(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未存在矛盾或矛盾已被合理排除;
(四)共同犯罪的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地位以及作用均已核对查清;
(五)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定过程符合生活逻辑与经验规则,由证据推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这难免会导致实践中将二者相混淆。实际上,“结论唯一”和“排除合理怀疑”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前者与“排除一切怀疑”是同义语,是指比“排除合理怀疑”更高的证明标准。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义不明确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将“排除合理怀疑”明确写入法律条文,但司法实践中对其内涵是否应予以明确仍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应按照英美法系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始理解在我国适用,但也有学者建议其内涵应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更可行,原因有二:一是明确证明标准有利于司法人员对刑事案件的统一把握。英美法系采用判例法,虽然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的“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但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形成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独特理解,其他法院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予以适用。
但是,在我国采用的成文法中,法官作出的前一项判决对后一项判决不具有约束力,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量刑程序都是由法官一个人完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法官个人感情、经验和性格差异的影响。
第二,做出定义是符合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裁判文书说理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存在合理性不强等问题,甚至一些地方法院在没有详细列举案件证据的情况下,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空洞的有罪判决。
三、证明中国标准的粗放性与不科学性问题仍未得到一个有效进行解决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程序确立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不仅适用于各类刑事案件,也适用于刑事案件,而且在调查结束时,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适用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规定对因证明标准不统一而导致的司法武断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也反映出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泛化、不科学的缺陷。尽管新刑事诉讼程序在刑事证明标准中纳入了“无合理怀疑”,提高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但无论案件类型和诉讼阶段,适用同一证明标准的弊端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案件的相关类型来看,普通刑事案件和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简易刑事案件和复杂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判案件和普通程序审判案件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第二,除了立案阶段的标准是“有刑事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外,严格要求调查结论的移送、审查起诉、起诉、有罪判决都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一般来说,人们的认知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诉讼各个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如果每个阶段都采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就不符合认识规律,也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提醒大家,如果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法官就可以根据这一内涵在判决书中说明案件的证据内容,指出如何排除合理怀疑,进而认定被告人有罪。这可以对法官起到制约作用,也是防止法官武断判决的有效机制。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