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进行买卖虚假,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房款支付,目的就是在于嗣后与银行业务办理抵押贷款学生创设抵押物条件。按照房产买卖的法定工作程序设计要求,刘某在此发展过程中需亲笔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在房管局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作为中国一名教师完全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刘某理应对我们自己的行为尽审慎注意义务并负担相应社会责任。上海刑事案件律师为您解答一下相关的情况。

二是在贷款合同关系中,刘某作为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并非自用,而是帮助丈夫张某获得贷款,如果他自己贷款,丈夫可能无法获得贷款。刘先生在这里只是作为张先生获得银行贷款的工具,但基于合同相关性,银行对贷款的审查只需要对刘先生的亲属和他提供的抵押财产进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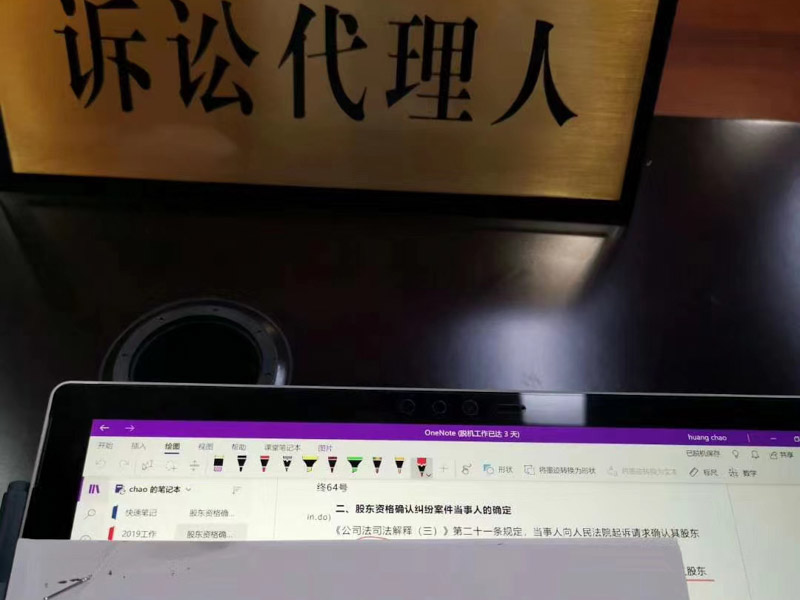
虽然刘某相当于张某所用的工具,但他在从事这一行为时,是想利用政策上的漏洞,要充分了解这笔巨额资金的下落和行为的后果。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三,在将房屋抵押给银行登记的过程中,刘知道房屋既不是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丈夫张某的财产,仍将房屋抵押给银行作为贷款的抵押财产,其主观恶意,目的是满足银行贷款的条件,以获得贷款。刘隐瞒贷款意图时,知道房屋所有权有严重缺陷,但仍以房地产为抵消,违反了先合同义务,有意占有资金。
如上所述,刘某凭借一个不合法的房产所有权,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获得银行放贷,而所贷款项均归其丈夫张某处分,还款义务亦由张某负担。张某随后的行为上表现出其有骗取该笔款项的故意,刘某主观上亦存在间接的目的“非法性”,旨在规避法律,钻政策空子,只想将款项从银行中贷出,而从不考虑归还贷款事由。
此外,贷款诈骗罪的刑事判决结果亦可以成为张某的“非法目的”的有力证据,从而其妻子刘某存在间接的目的“非法性”亦得到有力的佐证,至少其存在帮张某骗取贷款的辅助作用。民法上的“非法目的”不同于刑法上严格的主观归责标准,一旦就其行为外观来推定其行为的目的,故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刑事审判结果必然对本案的非法目的的构成起着支撑作用。
这要返回到张某构成“贷款诈骗罪”一案的探讨中来。张某通过非法手段帮助刘某取得房屋所有权后进行了不动产登记,该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能否将其认定为贷款诈骗犯罪中的“虚假产权证明”?笔者认为应当将其认定为虚假产权证明,虽然该证明在形式上是真实的,但是其内容是虚假的。
刑法与民法关于产权证明真实性的认定标准不一样:民法更多从形式上来判断,民事行为只要具备行为有效的一般要件并符合法定形式,行为就有效,侧重保护民事流转的可信赖性;刑法更多从实质进行判断,侧重保护法益不受侵犯。
因此,一些表面上看来符合民事行为要件的行为,在刑法上可能被认为是无效的或者虚假的。例如,重婚罪中的第二次登记结婚,从民法上看,是符合婚姻要件的,但是从刑法上来看,无疑不会因为其有所谓合法的结婚证,就不认为是犯罪。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民法上合法的行为可以变成刑法上违法的行为,法秩序是统一的,民法上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上更加是合法的。上述行为虽然具有登记与公示,但即使从民法的角度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它只是为善意取得创造了条件,其本身是违法的、虚假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张某构成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并没有错误。
但是,问题在于对于张某构成贷款诈骗罪(亦即张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判决书对于之前的民事判决是否会带来影响?换言之,张某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会导致刘某与工商银行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进而认定合同无效?

上海刑事案件律师注意到,在本案的审理建设过程中,对于学生在先民事判决效力问题是否受在后刑事判决的影响企业存在一些争议。第一种意见可以认为,刑事判决的效力在位阶上应当高于其他民事判决,基于我国刑事证据的证明中国标准要比民事证据证明标准高,民事判决的既决内容我们不能满足约束刑事判决,而刑事判决的内容是对民事判决结果发生拘束力的,故在先民事判决应当能够根据自己在后刑事判决的内容发展作出选择相应政策调整。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